外语学人 | 朱白兰先生与中大德语专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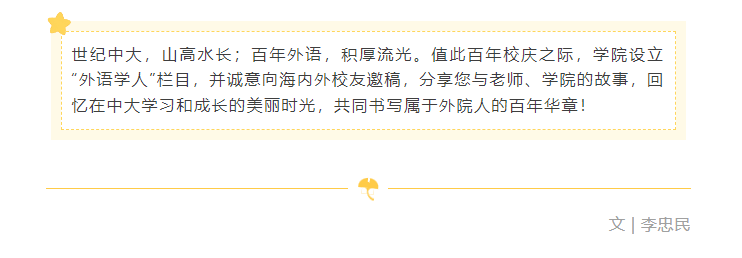

建国初期,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了大调整,学院制改为学系制。中山大学的工、农、医学院分别独立出去,文理部分不少优势学系及地质专业也合并到其他院校。瘦身调整后的中大只剩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地理系、中文系、历史系和西语系。西语系事实上只有英语和俄语(因中苏关系恶化,1960年后撤销)两个专业,无法满足正蒸蒸日上的发展需求。按学校扩充专业的规划,1957年法语招生,同年开始筹办德语,朱白兰先生正是这个时候为筹办德语专业从南京大学调入。
朱先生原名Klara Blum,犹太人,是知名的诗人和作家,也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女性,有“洋孟姜女”之称。她1904年出生于当年在奥地利版图内的一个边陲小镇,母亲是个女权主义者,因家道中落,嫁给了比自己大二十七岁,贪婪又粗暴的老财主。朱先生曾在诗中描述,她是“狐狸和夜莺的产物”。复杂的家庭环境,锻造出她一生追求正义的秉性和敏锐的诗人气质。高中刚毕业,她就开始在《维也纳晨报》发表诗作。1933年她反法西斯题材的诗歌,在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举办的赛事中获奖,受邀到苏联体验生活。在莫斯科她认识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创始人之一的朱穰丞,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追求让他们从相知到相恋,最终于1938年走到一起。可惜,这段幸福的时光只延续了四个月,朱在一次执行地下工作的任务中,被克格勃错当成日本特务秘密抓捕,从此音讯全无。Klara Blum为寻夫,不顾路途遥远,毅然踏上她诗中的“回乡之路”,历尽艰辛,足足花了两年的时间,来到正战乱的丈夫家乡——中国上海,过起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她不愿意接受丈夫已牺牲的事实,坚持终生寻找、等待,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国际版《牛郎织女》。直到解放后,在朱穰丞旧友的帮助下,作为“烈士家属”,改随夫姓,并兼顾自己姓氏的音意和喜爱取名白兰,加入了中国国籍,先后在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教授德语,才有了稳定的生活和工作。
朱先生知道中山大学要筹建德国语言文学专业,正是自己的强项,一来躲避南大东德官派专家的谗挤,二来扩大寻夫范围,便主动请缨,来到中山大学。她的学识和作品确保了这个专业有了顶梁柱和学术灵魂。朱先生虽然精通英、俄、法多种语言,但汉语确实欠佳。学校指定张仲绛教授为德语专业筹备组的组长,开始筹建德语专业的具体工作。
张教授系广东大埔人,原毕业于本校法学院,后又赴德,先学语言,后专攻德国法律,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后辗转回到本校法学院执教。学校改制后,法学院撤销,张教授因“历史问题复杂”,下放到学校总务处上班。他是爱国民主人士,工作积极,任劳任怨。民国时期,他曾担任省参议员,还短期出任过湛江市市长,有一定的行政工作经验和组织能力。
在招兵买马过程中,两位老先生加盟到德语教研室,一位是黄震庭教授,曾在柏林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成回国后,曾在旧中大执教。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弃笔从戎,先后担任过李宗仁、李济深和白崇禧的秘书,阶至少将。黄教授发音非常标准,对德语语音颇有研究,基础教学一流;另一位是张苏奎教授,他早年留德学军事,学成回国后,进入军界,跟随孙立人将军远征入缅,对日作战。解放前夕与八位国民党官员、将领联名在粤东发表《我们的宣言》,起义归顺,受过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复电嘉勉,由四野收编。他的德语张嘴就来,口语特别好。
在朱先生的建议下,德语教研室接收了南京大学当年的应届毕业生章鹏高老师,他是朱先生在南大时的得意门生。系里同时决定,从英语专业抽调一名骨干教师和一名留校学生分别到北外和上外,一边进修德语,一边学习他人的教学经验。
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德语专业1958年正式招生。之后又先后接收南大两位新毕业生,这里要说明一句,当时南大的德语专业的实力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外校进修的老师陆续回校后,在上外进修的张佳珏老师还担任了教研室副主任,教研室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充实。1960年开始,每年正常招生。
有德语是母语的诗人、作家朱先生坐镇,德语专业有理由雄心勃勃,大胆绘制自己的发展宏图,于是又从北外等单位调入四位老师,加上从自己58级和60级毕业生中,分别挑选两位留校任教,教师队伍增至十七人,正所谓人强马壮,具有充足的教学和科研力量。

朱先生除正常的高年级教学外,还肩负青年教师业务提高的重任,同时也是科研项目的定音锤。
当年的德语学生学习条件较差,听力教材只有一套“灵格风”,朱先生就挤出时间,为二年级以上学生录制听力材料,保证学生听力内容的多样化;当年德语学习的工具书奇缺,个别学生能碰巧买到的词典,也是解放前出版的。朱先生就提议编写,用自己的稿费从德国买回权威的Duden词典,选定词条,大家分工合作,共同努力,在短时间内集体完成了《简明德汉词典》,于1963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面世。这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德汉词典,不但填补了德语工具书出版的空白,也成了那个年代全国德语学生的首选工具书。德语专业从1964年起开始扩招,由一个班变为两个班,每班人数由十五增至二十人。一下子一个年级有了40个德语学生!1965年学制改为五年后,在读的德语学生共有五个年级,七个班,学生人数达到113人。笔者1961年入学,后又赶上学制改为五年,有幸经历和感受当时专业的飞速发展,见证了德语专业历史上的高光时刻。
我们二年级时虽然经常听朱先生的听力录音,但真正上她的课是三年级的事,四、五年级就主要是她的课了,是她上课最多、时间最长的一届学生。她教学态度认真,一丝不苟,讲解循循善诱,非常耐心;授课的风格深入浅出,遇到疑难的词语,不等学生发问,便立刻板书。她的字体苍劲有力,直上直下,也为班上许多学生模仿。为增强教学效果,她特别喜欢使用教具。来上课时肩上总是挎着一个米色大布包,装满上课有关的书籍、资料或图片。因为教材多是歌德、席勒原著,她怕我们所学的词汇和社会现实有些距离,观念受到影响,常会结合时势,增加一些现代题材。遇上好的翻译作品,也会即时引进课堂。记得当年何其芳《不怕鬼的故事》德译本一出,她就选了好几篇给我们做教材,还在堂上让我们担任故事中的角色,现学现演,既活跃了课堂气氛,也加深了我们对德语表述的掌握。影响一代人的主流话剧《年轻的一代》上演后,她马上选出关键的一场,让大家堂上分组讨论,共同翻译,她也当场评改,对比不同的用词,解析修改的理由。形成正式译本后,要我们开始课外排练,并在专业晚会上演出。兴许戏剧能多少释放她对爱人思念的情怀,我们对这种深刻的讲解和学以致用的方法感到受益良多。
除教学一流外,朱先生为人做事也给她的同仁和学生树立了榜样。她做事忘我敬业,鞠躬尽瘁;她为人公平正直、心地善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好善乐施,工资加稿费,收入虽然很高,但生活简单、衣着朴素。谁人有难,哪家有灾,只要急需或国家号召,她都会慷慨解囊。济难的小额捐款数不胜数,最大的一笔捐款发生在抗美援朝时,正逢她耗费几年时间完成的长篇小说《牛郎织女》刚在民主德国出版,为支援前线,稿费还没到手,她就去信全数捐给了当地的援朝委员会。笔者在当学生时就经历过一次,1965年越南开展反美救国斗争,中国政府全力支援,她就叫我帮忙,一起去越南驻广州领事馆,她明确表示自己是中国人,要为越南人们斗争尽一点微薄之力,向他们捐出了自己近两个月的工资。她到临终前也不忘吩咐,除了给保姆留点钱和物外,其余全部财物归还学校。

朱先生1971年去世,一生发表过诗歌五集,中、长篇小说三部以及大量的报道评论。这些作品大多以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为题材,历史跨度长达近百年。她应该是向德语国家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第一人,世界没有忘记她,二十多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派人专程来了解和实录朱先生生前的工作和居住地情况,我本人还参加了接待;目前在德国文学档案馆还珍藏着她未全文发表过的长篇小说《命运征服者》遗稿和不少与德国知名作家及友人来往的信件和资料,供人查阅与研究;在世界名都奥地利首府维也纳,还有一条新街用她的名字来命名。



朱先生在中国生活长达二十四年,多半时间是在是在中山大学度过的,占她职业生涯的三分之一。康乐园是她生命的最后一站,她是中大的骄傲,在校史上应该有一定的位置。

--- sysufls ---
供稿、供图:李忠民
排版、校对:李梓翊
初审:庄坚彬
审核:黄源穗
审定发布:常晨光、于海燕
欢迎投稿&加入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