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学人 | 区鉷:书人书事——书信中的戴镏龄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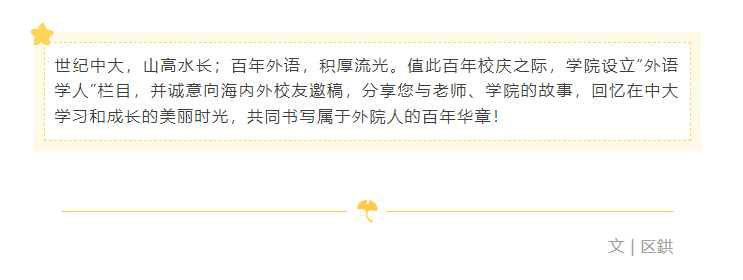
戴镏龄先生假如还健在,就是百岁老人。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只能以追思会的形式来纪念戴先生了。
作为学者、教授,其人生轨迹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留下的文字,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是也。比起规范严谨的学术论著,书信文字其实在不经意同更能显出人的本色。
戴先生基本上生活在前网络时代,信息交流主要依靠书信来往。有意思的是,他在日常生活中和在写给我的信里多次引用清代诗人吴梅村的诗句:“不好诣人贪客过,惯迟作答爱书来。”他写的信确实不多,已经发表的也只有写给我的一封长信。当时戴先生已经去世,王宗炎先生在编辑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4期下册(足球投注平台-足球下注app-足球投注网址 专刊)时觉得应该有中山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奠基人戴镏龄先生的文字,应王宗炎先生之约,我提供了这封信,加了注释,经他审读后以《已故戴镏龄先生谈外国文学和外语教育的一封信》为题发表。
戴先生在书信中谈得最多的是书,还有与书有关的人。
1995年我在美国杜克大学做研究教授时,戴先生曾给我一信,正文之外加了附言:“Susan Barile 的The Bookworm's Big Apple,由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出版,亟盼代购一本,照付书值,人民币或美金都可。又及。”这本书是纽约曼哈顿的书店指南,有了它可以按图索骥去逛书店。我买了这本书,回国后作为礼物送给了他。戴先生以前就去过哥伦比亚大学书店。1992年6月他在美国探亲,6月2日从纽约给我写信道:“纽约书市甚大,但太分散,披沙拣金,劳而少工。43年武大毕业生王君来电话,说愿在因公赴非洲前,和我到哥伦比亚大学书店看看……此书店确有学院味,架上大部分为古今经典名著。但他坚持代付书费,我无意多买令他花费,只挑选了两本便宜的以资应付。但在书店逗留翻阅时间甚长……昨日儿媳驾车送我至纽约皇后区图书分馆看出售旧书,选了三种,以Edward Gibbon的《罗马衰亡史》最令我惬意。此虽为节本,然保留了原著的主体,首尾完整,精华具在,校注翔实,精装大本内容仅 1000页,便于阅读及携带。此书向少善本,牛津World’s Classics只印行了 Gibbon 的自写简传。近年每人丛书始将其重印,大版六本,不便诵读。本夙负盛名,然沿袭原来印体,错误竟至近七十处之多,令人遗憾……付书价时,图书馆长钱女士坚不肯受钱,以其父为我之亡友。她在五十年前还是孩提之童,对往事不甚了了。此番不期而遇,尚以旧情为念,代我掏腰包还图书馆的账,亦在纽约买书一佳话也。”
戴先生不仅对版本了解甚多,而且对读过的书籍十分熟悉。有一次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钱钟书的张明亮老师碰到几个典故,“遍查未获”,来信请我代向戴先生请教,戴先生写短简给我,一一作答。其中有一句英语诗,张明亮只知道其作者是美国诗人Dorothy Parker。戴先生写道:“Dorothy Parker有打油讽刺诗集Not So Deep as a Well, 1936年印行,可找来查。我记得出自她的‘News Item’一首中。手头无原书。”还有一次,当时在中山大学外语系任教的英国教师Maria Jaschok研究中国妇女问题,不知“瘦马”何解。戴先生又写短简让我转告:“请告Dr. Maria Jaschok,据翟灏《通俗编》第22卷,‘瘦马’典故出于白居易《有感》诗,为后来所本。德国出生的汉学家艾伯汉(Wolfram Eberhard)教授认为此称呼在扬州源于16世纪。他说,现代台湾也有以马指女情人的粗话。翟书易得,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复印过,又及。”(现在叫“马子”了。)
由于深谙中外经典,旁征博引,自然会用比较的眼光考察书籍的内容。戴先生多次强调,做学问到了化境,不知不觉就会进行比较和对比研究,将材料加以辨析。戴先生是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导师。我的硕士论文选题是郭沫若《女神》与惠特曼《草叶集》的比较研究。郭沫若提到“司春女神”,戴先生在给我的信里说:“希腊罗马未闻司春女神。希腊的 Persephone(罗马作Proserpina)被Pluto劫入下界,只春天及夏天回到人间,又为谷物的神,司生长,可作司春女神看,但古人作品中不将其作司春女神而加以歌颂。希腊Adonis代表青春,却为男性美少年。英国May Day(实为春节,因英国春天迟到)的May Day Queen倒是真正司春女神的象征。记得文艺复兴时一幅名画Printemps (春天)中全为一群跳舞的女性,惜手头书散失,记不起作者是否为Titiano。”
我常常惊叹于前辈们强大的记忆力。(在这方面陈寅恪先生也有轶事。)后来在戴先生家里看到一副集句联:“旧书不厌百回读,明月自照千家墀。”联想起先生在1987年5月30日在信中教导我“对柏拉图应深入精读,有所领悟”,才明白超强的记忆只是“薄发”,背后的“厚积”就是“深入精读,有所领悟”,“不厌百回读”。先生对我讲过一段发生在他的同辈人中的文坛逸事:某公自称读书破万卷,洋洋然有大师之风。一日,有人效武林打擂事,携来书籍数册,约此公专门切磋此数册书。某公心虚,期期艾艾,终托词而遁。这件事我写人了随笔《旧书明月伴吾师》。
对于和书有关的人,戴先生书信中有褒有贬,但贬之极少。他老人家在学界的口碑是“忠厚长者”。更多的是感叹“时序飞腾,疾于石火电光”,而书友凋零。1989年我在剑桥大学做博士后,当年1月7日戴先生给我一封用英文写的信,有一大段提到一个月之内北京大学杨周翰、王瑶、岑麒祥和南京大学法语教授何如先生离世。杨周翰先生去西安看病(淋巴癌),两度登不上飞往西安的飞机,只好乘火车去。到了西安火车站他已经筋疲力尽,要用担架把他抬去医院。过不几天,杨先生就病逝了。字里行间,戴先生唏嘘不已。同年8月戴先生来信说:“世界各地不幸的事时有发生。我个人死去不少亲戚。老友中逝世的包括谢文炳及张月超等,令人不快。”
即使感到岁月催人老,戴先生仍然忘我工作。他在美国探亲期间还念念不忘所指导的博士生。他来信说:“xxx(该博士生)来信称,深大坚要他去上课,不得已暂去了。论文烦你过目,对他要严加督促,以竟全功。”“此论文内容会有人认为偏僻,各人有各人的趣味。”接着他就为其邀请答辩委员做了周到安排。
书信是人的剪影。我保存着戴镏龄先生写给我的21封信和短简,并把它们复印了放在中山大学外语学院英诗研究所的书柜里,供年轻教师和学生研读。希望他们心目中也存留一点戴镏龄先生的影像。
戴先生仙逝后,师母把他的藏书全部捐给了中山大学图书馆。捐书之前师母让我挑一册作为纪念。我选了一部线装的《三台诗林正宗》,师母题了字。
(原载《中山大学报》2013年5月14日,第3版,本文略有删改)
--- sysufls ---
供稿:区鉷
整理、校对:冯羽轩
排版:李梓翊
初审:庄坚彬
审核:黄源穗
审定发布:常晨光、于海燕
欢迎投稿&加入我们

